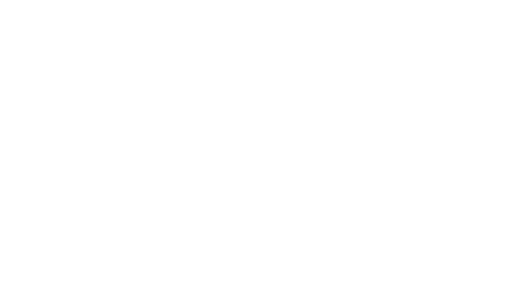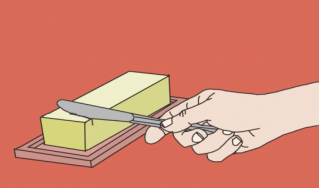噬菌体与冷战时期阿富汗的霍乱斗争
苏联时代的疗法能否提供一种对抗耐抗生素超级细菌的新方法?

噬菌体攻击细菌的彩色透射电子显微照片。
1960年8月,当Zinaida Plankina抵达喀布尔的中心医院时,那里已经挤满了600名城里病情最严重的霍乱患者。阿富汗政府找到了苏联流行病学家和她的专家团队,基于她早期成功地阻止了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的霍乱爆发。Plankina选择的工具是被称为噬菌体的细菌摧毁病毒,她的团队携带了足够治疗阿富汗每一个霍乱病人的噬菌体。
飞机着陆后不久,Plankina和她的同事与Aliabad总医院的首席医生会面,她认为这将是一个关于如何最好地管理噬菌体的计划会议。相反,阿富汗医生告诉她,他们不会使用这些药物。他们说,这些治疗会干扰医院已经在使用的美国供应的抗生素。普兰基娜和她的噬菌体不受欢迎。
这位流行病学家无意中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与科学关系更少、与政治关系更大的争论中。支持抗生素的人和依赖噬菌体的人之间的斗争是冷战时期的一场小冲突,阿富汗的医生和病人夹在美国和苏联交战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之间。
在冷战期间,阿富汗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非常复杂。
1947年,英国离开印度次大陆,给该地区留下了一个政治空白。当时的阿富汗总理沙阿·马哈茂德·汗(Shah Mahmud Khan)明确表示,他打算与美国结盟,将美国视为英国的天然盟友和继任者。但美国对阿富汗没有什么兴趣,而是寻求与阿富汗的邻国和政治敌人巴基斯坦结盟。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关系,这削弱了美国与阿富汗的关系。
另一方面,苏联与阿富汗接壤,这让他们在维护较贫穷邻国的政治稳定方面有了既得利益。从1955年到1979年,苏联领导人向境况不佳的内陆国家提供了今天价值93亿美元的援助。苏联的对外援助也向世界表明,苏联的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出口,而且是成功的。如果苏联在阿富汗的计划成功了,他们就离赢得冷战的零和游戏又近了一步。
但当1960年普兰基纳抵达阿富汗时,阿富汗与苏联的政治联盟还没有巩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仍有一种与美国结盟的愿望。阿富汗医生是那些需要美国支持的人之一,包括抗生素,当时正经历着发现的“黄金时代”的神奇药物。
霍乱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通常是致命的腹泻疾病,是由霍乱弧菌细菌。几个世纪以来,霍乱肆虐了许多社区,但疫情的爆发规模很小,而且是孤立的,直到1817年,国际贸易网络的发展导致了第一次霍乱大流行。霍乱始于印度,蔓延至俄罗斯。38年后,英国医生约翰·斯诺著名的显示霍乱通过被污染的水传播基于斯诺发现的卫生措施减缓了疾病的传播,但这些改善对那些已经患病的人没有什么帮助。
Snowmapfinal2.jpg.

伦敦医生约翰·斯诺调查1854年霍乱爆发的详细地图,他追踪到一个受污染的饮用水泵。
的韦尔科姆收藏馆
在下一个世纪,对抗细菌疾病的强大工具出现了。
磺胺类药物在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霉素紧随其后。这些抗生素可以治愈人,而不仅仅是治疗症状。到1960年喀布尔爆发霍乱时,许多抗生素被用来治疗各种细菌感染,包括霍乱。部分原因是,自二战以来,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四年多。
但是,抗生素的益处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就对毒品进行了战略限制。虽然抗生素生产在战争期间蓬勃发展,但美国军方一直没有向苏联盟友提供抗生素,直到战争接近结束。
作为回应,苏联科学家继续研究基于噬菌体的疗法,这项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战争结束后,苏联仍然致力于噬菌体的发展,以至于在1953年,它制定了法规,巩固了噬菌体作为细菌感染的主要治疗手段的地位,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研究中心,以提供稳定的药物供应。
虽然苏联人很早就开始采用噬菌体疗法,但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分离出这些了不起的病毒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英国细菌学家弗雷德里克·特沃特(Frederick twot)就意识到,那些中枪或受了外伤,然后在池塘或其他水体中待了很长时间的士兵,往往比那些掉在陆地上的士兵活得更好。他对这种现象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从这些水源中提取水样本,很快就分离出一种令人费解的物质。特沃特发表了他的发现的《柳叶刀》在1915年,他描述这种物质是由“超微观病毒”组成的。但特沃特为自己的判断打了个擦边球,他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微小的细菌”或某种变形虫。
dherellefinal.jpg

法国细菌学家Félix d 'Hérelle,约1905年。
法国国家图书馆
幸运的是,特沃特没能完全理解他的发现。Félix d 'Hérelle是一位不安分、喜欢冒险的法国微生物学家,他开始研究特沃特的发现以及它治愈受伤士兵的机理。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d 'Hérelle很快确定了这种神秘的病原体是寄生病毒,他将其命名为噬菌体(噬菌体在拉丁语中是“吃”的意思)。很快,'Hérelle发表了他关于这些以细菌为食的人的发现。
世界似乎不仅准备接受噬菌体,而且准备接受一种新的医学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治愈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噬菌体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作者辛克莱·刘易斯1925年的小说,阿罗史密斯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医生用噬菌体拯救热带岛屿上爆发瘟疫的人们的故事,第二年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D 'Hérelle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寿命较短的噬菌体实验室,并周游世界,获得了支持针对痢疾、鼠疫和霍乱的噬菌体项目的奖项,并在耶鲁大学担任了五年的教授。到20世纪30年代,噬菌体加工厂开始在全球各地开业,包括美国、法国和巴西。
georgeeliavafinal.jpg

格鲁吉亚微生物学家George Eliava,未注明日期。
维基共享
到那时,d 'Hérelle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国持续存在的政治动荡感到幻灭。在这里,他和其他科学家可以安全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当他的前同事、前苏联细菌学家乔治·埃利亚瓦(George Eliava)给'Hérelle提供了一份工作,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埃利亚瓦细菌学研究所(Eliava’s Institute of Bacteriology)帮助建造噬菌体中心时,这位法国人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Eliava的Brainchild计划作为庞大的,17公顷的世界级设施。该计划由斯大林亲自批准,包括Eliava和D'Hérelle,实验室,诊所甚至a的住宅植物园,所有与法国图案。D'Hérelle的妻子Marie在1934年和1935年在学院共计12个月。
但在1935年底,政治氛围发生了转变。Lavrentiy贝利亚他是格鲁吉亚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亲密盟友,也是埃利亚瓦儿时的对手。不久之后,d 'Hérelle和他的妻子以需要完成巴斯德研究所的工作为借口,从格鲁吉亚港口城市巴统登上了一艘意大利船。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不幸的是,在1937年斯大林执政期间,伊利亚瓦在贝利亚的命令下被谋杀大清洗.
世界似乎不仅准备接受噬菌体,而且准备接受一种新的医学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治愈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
D 'Hérelle继续研究噬菌体,但从未得到他想要的认可。他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奖,但从未被选中。他的科学方法不断受到攻击,他在维希时期的法国被软禁。他于1949年去世,当时抗生素的黄金时代刚刚开始。
尽管有这些损失,苏联的噬菌体研究还是蓬勃发展。苏联各地开设了几家研究中心,包括伊莱亚瓦的实验室,该实验室于20世纪30年代末建成。第比利斯的实验室现在被命名为Eliava研究所,仍在为格鲁吉亚及其周边国家的公民生产噬菌体。
直到1954年,一种治疗霍乱的有效噬菌体才被发现,当时在顿上罗斯托夫抗鼠疫研究所的苏联研究员亚历山大·格里戈里维奇·尼科诺夫终于成功了。Nikonov的成功需要在感染霍乱的豚鼠身上进行细致的试错实验,以及开发新的噬菌体生长培养基,其中包括“胆汁、小肠内容物和Tyrode溶液中的小肠碎片”等成分。
1958年,当霍乱在东巴基斯坦偏远地区的一座城市爆发时,苏联抓住了这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噬菌体至少和对手的抗生素一样有效。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苏联特遣队已经为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提供了治疗;没有一个人出现复发迹象。
尽管有了一种经过验证的霍乱治疗方法,普兰基纳和她的同事们在1960年遭遇的霍乱爆发尤其令人生畏。在阿富汗,霍乱是一个普遍问题——在过去的40年里,阿富汗经历了几次霍乱爆发——但现代交通工具扩大了霍乱的传播范围,加快了它的传播速度。普兰基纳也认识到一些传统也促进了这种传播。灌溉沟渠被用作清洗尸体和漱口水的来源。喀布尔的霍乱疫情后来被追溯至一名妇女,她曾从灌溉沟里喝水,在更上游的地方,哀悼者曾在那里清洗贾拉拉巴德一位霍乱患者的床单。
afghanvaccineresearchcenterfinal.jpg

阿富汗疫苗研究实验室,约1960年,从阿富汗:现代方式的古老土地, 1961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
阿利阿巴德总医院的医生最初试图隔离病人,但没有效果;要想迅速隔离人群以阻止传播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们使用的美国抗生素土霉素,只有50%的效果。
面对越来越多的病例,医院的医生开始检测和隔离所有与阳性病例接触过的人。但他们来得太晚了。疫情激增,使医护人员无法对患者进行检测。到1960年8月Plankina到达的时候,Aliabad总医院的600张病床都已坐满,霍乱患者挤在一起,但没有适当的隔离措施来防止在医院内进一步传播。
10月2日,另一家医院神经内科病房的一名患者因腹泻死亡。一名负责清理尸体的医院工作人员和一名给病人喂食的厨师也生病了。到10月6日,医院不同地区的12名患者出现了与霍乱相似的症状。由于这些病人分散在医院各处,不在霍乱病房内,不堪重负的阿富汗医生未能识别出这些病例是霍乱。
当Plankina听说了胃肠炎的神秘发作后,她抓住机会为这些病人检查霍乱。在病人(包括两名昏迷的病人)检测呈阳性后,Plankina秘密地用噬菌体治疗他们。到了第二天,这些病人的病情好转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阿富汗的医生们放弃了抗生素,转而使用Plankina的噬菌体注射。据报道,当地人称这种疗法为“圣水”。
1960年10月至12月期间,Plankina和她的同事给1600名医院员工接种了噬菌体。那年冬天,阿富汗公共卫生部长召集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外援,并说服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团队前来帮助Plankina和她的同事为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接种疫苗。这个国际小组使用了550多升霍乱噬菌体治疗了2.7万多人,其中一些人生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危险的村庄中。在三年的随访监测中,没有一个接受噬菌体治疗的人患上霍乱。
afghanmountainvillagefinal.jpg

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的一个偏远村庄,约1969年。
哈里森·福尔曼/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图书馆
尽管这项医疗使命的成功显着,但普拉斯娜州的一份关于Plankina工作的英语文章存在,由世卫组织出版。她和她的同事们回到了苏联,因为他们来了很多粉丝。毕竟,她仍然是苏维埃,她的科学仍然被视为其他阿富汗人和世卫组织代表团成员。
为什么没有有进取心或雄心勃勃的美国研究人员采取这种令人信服的治疗方法?很可能英语世界从来都不知道她的努力。帮助分发噬菌体的小组是通过d 'Hérelle与噬菌体有联系的法国小组,以及当时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捷克小组。
说到美国的噬菌体研究,自从Plankina开始她的阿富汗任务以来,60年来几乎没有增长。但是,随着医生们面临一个日益令人担忧但已被长期承认的问题,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抗生素被发现后不久,细菌耐药性的迹象开始出现。科学家,比如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塞尔曼Waksman早在1945年,他就意识到细菌开始对青霉素产生抗药性。两年后,Waksman细菌显示出对链霉素的耐药性。要克服不断增长的耐药性,需要新的、所谓的广谱抗生素,但细菌几乎立刻就显示出对这些新药的耐药性迹象。Waksman甚至在对实验豚鼠进行疗效研究时发现了对链霉素的耐药性迹象。
比利时微生物学家莫里斯·韦尔什确信耐药性是不可避免的,并在1952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这一点。制药公司的应对措施是引入固定剂量的联合抗生素,以克服日益增长的细菌耐药性。这些药物将两种,有时是三种抗生素混合在一片药中,但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细菌耐药性的增加而被禁用。
oxytetracyclineadfinal.jpg

广谱抗生素土霉素的广告,约1979年。
的韦尔科姆收藏馆
土霉素,1960年在喀布尔使用的抗生素,属于广谱家族。这种淡黄色的药物是由辉瑞公司的科学家在1952年开发的,是第一种完全由制药公司生产的抗生素。该公司将其命名为土霉素,因为它在土壤样本中被发现,并被证明能成功治疗多种细菌感染。
尽管抗生素耐药性不断增强,但噬菌体治疗从未在抗生素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得到普及。历史学家推测,由于抗生素在其发展的早期有如此多的希望,科学家们努力理解所有抗生素耐药性的必然性。当然,这些研究人员有理由保持乐观。科学家们正在快速地研制抗生素,当耐药性被发现时,新的抗生素,如万古霉素,就被制造出来了,他们通常相信没有细菌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这种对抗生素的无限支持及其前景得到了冷战及其对美国和苏联科学的影响的支持。这场冲突影响了政治分歧双方的科学领域。例如,苏联科学家推广了他们自己的遗传学,这种遗传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支持的理论,主要是因为它不是西方的。
为什么没有有进取心或雄心勃勃的美国研究人员采取这种令人信服的治疗方法?
美国人同样鄙视苏联的医学。在中央情报局1951年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人士对苏联医学状况进行了调查,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老式医学”。冷战对这种分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隐瞒了苏联在噬菌体研究上取得成功的知识,但美国科学家对抗生素坚定不移的追求和对噬菌体的放弃,与类似的冷战政策一致,这有利于采用本土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确实开发了自己的抗生素,名为谷氨酰胺s,尽管缺乏资源和其他因素阻止了他们开发其他抗生素。)
美国人一直不愿寻求噬菌体疗法,部分原因可能是冷战的后遗症,但资金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噬菌体作为自然存在的有机体,不能申请专利。
glaxoantibioticproductionfinal.jpg

帕克,达维斯研究实验室在底特律,密歇根州,加利福尼亚州抗生素生产。20世纪40年代。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噬菌体疗法实际上是被禁止的。然而,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至少让一些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这种病毒的潜力。
2016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一个医生团队成功游说FDA批准紧急使用噬菌体,以治疗该校精神病学教授汤姆·帕特森(Tom Patterson)感染的噬菌体不动杆菌baumannii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耐多药细菌。
这种治疗的显著效果与50多年前Plankina患者的治疗效果相似。在静脉注射噬菌体后,帕特森在三天内从长达数月的昏迷中苏醒过来。此后不久,他就完全恢复了健康,重返工作岗位。这一成功以及其他一些成功,促使几名研究人员在2018年启动了该校创新噬菌体应用和治疗中心,以抗击耐抗生素疾病。
圣地亚哥实验室是一个例外。许多美国研究人员怀疑噬菌体的功效,有一些证据支持这种怀疑。例如,最近的研究发现,人体可以迅速释放噬菌体。在这种情况下,噬菌体没有在体内停留足够的时间来消灭细菌,导致治疗无效。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格鲁吉亚科学家已经成功地用噬菌体治疗了病人。任何认为它们无效的说法都与他们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和临床经验背道而驰。如今,患者可以购买现成的噬菌体来治疗特定的细菌,比如葡萄球菌,还可以在三天内为其他更复杂的细菌感染接受特制的噬菌体鸡尾酒。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伊莱亚瓦研究所的医生们制作的噬菌体疗法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对他们来说,治疗很有效。
eliavainstitute2005final.jpg

噬菌体研究人员Nina Chanishvili (左)和Ketino Porchidze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Eliava研究所的研究。
Vano Shlamov/法新社,盖蒂图片社报道
加拿大人阿尔弗雷德·格特勒(Alfred Gertler)就是这样一个例子。2001年,他成为格鲁吉亚第一个接受噬菌体治疗的西方人。一年前,他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纽约时报杂志关于噬菌体。这篇文章强调了它们在西方的缺失,尽管格鲁吉亚科学家成功地使用它们来治疗细菌感染,例如葡萄球菌这种细菌长期折磨着格特勒的脚,即使在接受了近四年的抗生素治疗后,这种细菌仍在继续。
格特勒知道他很快就会失去他的脚,他把噬菌体治疗视为避免截肢的最后机会。他很快发现噬菌体在西方并不是一种被批准的治疗方法。所以在2001年初,他花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飞到第比利斯开始治疗。
在Eliava研究所接受了两周的治疗后,Gertler痊愈出院了。尽管取得了成功,但此后只有少数西方人在格鲁吉亚接受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