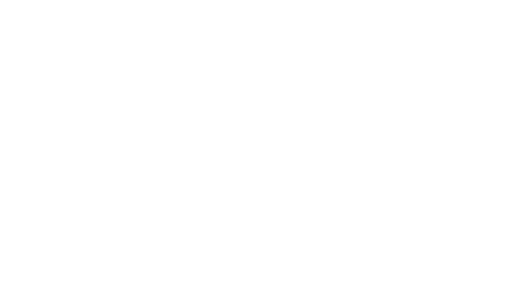老的药
一个医学博物馆描绘了爱丁堡的智力高峰和犯罪低谷。

苏格兰外科医生和艺术家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的一幅插图展示了从他的肩膀上截肢的一只手臂大手术的插图(1821)。
外科医生的大厅博物馆
苏格兰爱丁堡
museum.rcsed.ac.uk
几年前,我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时第一次接触到外科医生厅博物馆。我在尼科尔森街(Nicolson Street)的这座建筑前走了好几个星期,直到一块宣传博物馆与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关系的招牌把我吸引了进来。一进去我就迷上了。尽管这里的空间很狭窄,展览也在不断老化,但展品和故事与爱丁堡的医学史交织在一起,令人印象深刻。尽管这些展览看起来很古老,但医学主题以及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让人感觉非常现代。我回来过很多次,经常带着朋友和熟人。
当我在2016年回到爱丁堡时,这座博物馆——尽管它的名字是复数——是我重游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最近的翻修增加了一个现代的外观和额外的空间,但外科医生大厅或多或少保持了原来的样子,里面收藏着医疗器械(无菌时代的木柄截肢锯)、湿标本、绘画(查尔斯·贝尔爵士的一幅破伤风病人的画)和一些奇怪的东西。互动展示,如解剖剧院和解剖桌,使它感觉不像一个博物馆的博物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不像过去几年,我发现自己不再独自在房间里。
该博物馆是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的一部分,该学院成立于1505年,原名为爱丁堡巴伯外科医生。该学院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医学组织之一,在1832年对公众开放之前,它的收藏被用作医学生的资源。
在大学的早期,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于不给病人做手术的医生。外科医生和理发师共享一个行会,甚至把女性也包括在内。战场是肮脏的,混乱的,血腥的,因此被认为是粗糙的。手术往往会导致死亡,而且是在最后关头才进行的,没有麻醉剂,而且越快越好。几百年来,它一直是一种粗糙的速度游戏。这种情况在18世纪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法国,人们对各种知识的渴求迅速增长,这提高了外科医生的地位和技能。在革命后的法国,所有医生都被要求接受外科手术培训,外科医生也被要求接受医学培训,这一制度影响了英国的医疗实践。
法国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苏格兰得到了呼应。爱丁堡是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故乡,它成为苏格兰的学术中心,被称为“北方的雅典”,影响了苏格兰的医学教学和实践方式。爱丁堡的知识精英人数不多,他们大多彼此认识,或至少彼此认识,不管纪律如何。例如,解剖学家经常和艺术家朋友一起工作,或者就像贝尔一样,自己就是艺术家。贝尔是一名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他是第一个在脊髓中区分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人,并使用他的艺术技巧来记录他的发现;这种对身体的写实描绘反过来影响了解剖学的教学方式。
早在18世纪20年代,这座城市就因其尖端的医学和外科手术而闻名,吸引了来自英国、欧洲和英国殖民地的学生。亚历山大·门罗(Alexander Monro)于1719年被任命为皇家学院第一位解剖学讲师,是18世纪的主要医学界人物之一。他在学生和学者面前表演解剖,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对医学和外科很重要,而且对宗教理解、法医学和艺术也很重要。他的《人体骨骼解剖学(1726)和苏格兰天花接种的记述这本书影响广泛,并被翻译成法语、德语和其他语言。门罗还被任命为当时刚刚成立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的国际声誉提升了学院的地位。那么,也许博物馆里展出的最古老的物品曾经属于门罗就再合适不过了——1718年学院送给他的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落座大钟,里面有门罗解剖并制作的一个孩子的骨骼。
但是,大学里解剖尸体的主要来源是死刑犯,而不是儿童——至少在1823年之前是这样。当时,《死刑判决法案》(Judgment of Death Act)减少了苏格兰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尸体供应也开始枯竭。作为回应,教授们慷慨地购买新鲜的尸体,这导致了盗墓和“复活派”的兴起。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尔(William Hare),他们在博物馆中占有显著地位。1827年,这对夫妇卖掉了伯克家中自然死亡的房客的尸体,赚了一大笔钱。当他们得知学院的解剖学讲师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为每具尸体支付8到10英镑时,他们决定“帮助”其他人一起死去,并从中获取战利品。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在被发现之前杀死了16个人。
由此产生的审判轰动一时。野兔因为告发了他的伴侣而获得了豁免权,而伯克则在两万到三万名旁观者面前被吊死在爱丁堡城堡的台阶上。公众的强烈抗议和新闻的狂热围绕着伯克的行为和他的处决,最终导致法律的变化,使无人认领的尸体可以提供给医生作为教学目的。
在博物馆展出的是一个柏克脸部的石膏面具和一个用他的皮肤做的皮夹。当时的一个侧影带着病态的喜悦叙述着那次处决:
在那个不幸的人被关起来的那段时间里,在广大的人群中,没有看到一丝怜悯的迹象,相反,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庆日的欢快神情,人们在这一场合随意地谈论着双关语和笑话。
外科医生厅博物馆还收藏了另一个阴谋和谋杀的著名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伦敦更常与福尔摩斯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没有爱丁堡,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就不可能存在。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和故事的作者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于1876年至1881年间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学医,师从法医病理学先驱约瑟夫·贝尔(Joseph Bell)。在博物馆里展出的一封1892年道尔写给贝尔的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贝尔的影响:“我最肯定地感谢你,夏洛克·福尔摩斯。”
道尔在自传中叙述了福尔摩斯的创作过程。“我想起了我以前的老师乔·贝尔,想起了他那张鹰一般的脸,想起了他那古怪的行事方式,想起了他那捕捉细节的诡异技巧。”贝尔的肖像挂在博物馆里;他直直的眼神和孩子气的脸确实有点像流行的福尔摩斯形象。
和福尔摩斯一样,贝尔提倡仔细观察;和小说中的侦探一样,他有时也会被警察召去协助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件。他可以通过观察陌生人的生活来推断他们的亲密细节,他经常展示这种能力给他的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关于观察的讲座,他把手指放在一个装满液体的管子里;然后他举起一根手指放到唇边,对这种味道做了个鬼脸。他把管子递给他的学生,他们都尝了尝。然后,贝尔惩罚了他的学生,因为他们错过了他的把戏:他把一根手指伸进管子里,舔了另一根。
和贝尔的学生一样,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外科医生大厅时,我充满了敬畏之情。当我再次访问爱丁堡时,我仍然是那个热情的学生。从医学进步,到刑事司法,再到侦探小说,外科医生厅博物馆展示了这座城市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如何成为医学界的中心的。如果你碰巧在苏格兰,对历史、医学或恐怖感兴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博物馆。